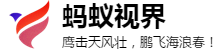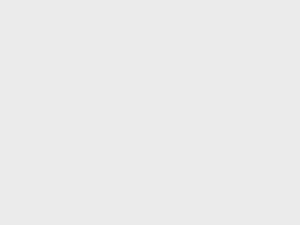- A+

新京报讯 葛存壮说他在步入老年以后,对表演的心得多了些,但实践的机会少了。我提到他在《街上流行红裙子》那分外醒神的表演,他谢谢我还记得那个吹箫的老人。我要谢谢他,曾给我带来这么温润的银幕记忆。
银幕上“反派”这么多
1949-1966,一般被史学家称为“十七年电影”。可以说,这十七年是中国电影与普罗大众最为亲密的十七年。电影这舶来品,从摩登大都市真正走向了田间垄头,军队、厂矿、学校。这是以前的电影工作者所期盼已久却迟迟没有实现的观影景观。它使电影这一机油味和铜臭味并重的现代化产物,在方圆九州,切实拥有了民间性。
在那样一个火红的年代,除极少数影片外,无外乎战斗和建设这两大主题。当时的国人,最热衷的还是战斗,是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毫不留情的宣战,并一往无前地付诸行动中。有人代表正义,就有人代表罪恶。
在十七年里,最为观众熟知的反面形象,即陈强、刘江、方化和葛存壮。除此还有李孟尧、方辉、安震江、李林、周文彬,以及更杰出的谢添和李纬,但在更普遍的“审美”上,他们不及陈、刘、方、葛更深入人心。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国人对电影的理解,大多是从戏曲中获取经验。陈、刘、方、葛这四位的表演更为集中、饱满,或者说更为老派。后来一些学者称之为脸谱化的表演,但其实跟“文革”中的样板戏,那些恨不得把人物身份、性格写在脸上的角色比起来,他们的表演还是有一定的人味、人情。
葛存壮的“日本军官”更像纸老虎
具体说到葛存壮,他和方化有一点非常接近,经常以侵华日军的中下级军官示人。两人实际生活中,都能说上几句日语。而日式中文,如“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也正是经这二位之口,而成为几代人一旦玩笑起来时的常用语。
相较而言,方化出演的日本军官,更为阴狠、独断。而葛存壮一旦蓄起仁丹胡来,既有外热内冷的随和,又不乏色厉内荏的虚张。假如说方化更像一个随时准备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那么葛存壮则是一架得过且过的战争机器,一枚貌似铆得很紧的螺丝,更准确地说,是个手一戳就破,火一点就着的纸老虎,更像一个颇有自知之明的跳梁小丑。
是的,你可以说葛存壮的表演是打上了相当显著的、先入为主的标签,也可以说他适应了当时中国电影的表演美学。但他的尽心尽责,如绿叶般衬托出一朵朵红花的傲然绽放,是时代浪潮裹挟下的一泓可供想像的逆流。
要说的是,葛存壮所饰演的反面形象,大多展现他们不一味地凶狠和奸诈,《红旗谱》里的大恶霸冯兰池是个例外。在那部影片里,我们看到这位老艺术家在壮年之时,那双不大不小的眼睛里所暴露出来的凶光。但之后,葛存壮再也没有过如此霸道的表演,他后来的恶形恶状,都有一定的喜剧效果。
“马尾巴的功能”影响了葛优表演
在我看来,葛存壮电影表演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是在“文革”期间拍摄的《决裂》。这部当时“又红又专”的影片,现在看来,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了,说的是工农兵大学如何改变教育格局的故事。葛存壮出演一个走“封修”路线的教员孙子清,这是个且迂且腐的、尚待改造的知识分子。而葛存壮煞有介事地在三尺讲台上所宣讲的“马尾巴的功能”,其一脸严肃令人忍俊不禁。也正是从这部电影当中,这段小小的表演里,能让我们相信,他的爱子葛优,其冷面幽默的表演多少来自于他的血脉之中。只是葛优的表演,间离效果更强,更容易心不在焉。
说起葛优的名字,老嘎本来要给小嘎命名为“忧”,是指葛优小时身体不佳,很让这位父亲操心。后来才改为优,不仅仅希望他各方面都优秀,也有对他将来子承父业的期许。优在古语里是“优伶”的意思,也就是演员。好在,长江后浪推前浪,葛优现在已成为具时代标志性的演员。父子俩只合作过一部电影,即司徒兆敦执导的《父子婚事》。印象中,这是葛存壮惟一一次演主角。
印象最深的是吹箫的老人
说回到葛存壮,予我印象最深的表演,还不是那部让葛老爷子夺得金鸡奖最佳男配角的《周恩来――伟大的朋友》中饰演的国画大师齐白石(他后来在电视剧《徐悲鸿》饰演过同一角色),虽然葛存壮演来,有着这位大画家所特有的古风古韵,以及深藏内里的赤子之心、分寸感和一份功深熔琢的气派,颇有说服力,而是在《街上流行红裙子》中,那个在上海公交站避雨的盲人。
在这个大都会渐渐安静下来时,老人吹起了箫,像是在等一个美丽的姑娘,又像默数着时光静静地流淌。葛存壮是这部本就洋溢着淡淡诗意影片里最动人的存在。在社会急速转型的阵痛期,雨声和箫声共鸣出一种更恒定的、事关生命的喟叹。这大概也是葛存壮戏份最少的一次表演,却有着不事张扬的点睛功用。葛存壮没有多少表情,脸上偶尔挂着一丝淡淡的笑,却犹一脉轻缓的心香在飘散。
2008年,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葛存壮,在他北影的家里。老人很随和,我们基本是站着聊天,从一个屋子走到另一个屋子,看得出,他身体还很好。我提到他在《街上流行红裙子》那分外醒神的表演,他说他在步入老年以后,对表演的心得多了些,但实践的机会少了,他谢谢我还记得那个吹箫的老人。我要谢谢他,曾给我带来这么温润的银幕记忆,现在,这真的成了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