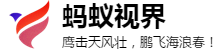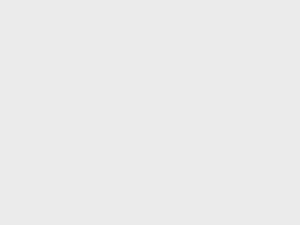- A+
前言:
从1966年到1969年正在读高中或初中的各三届学生,被统称为“老三届”。这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新人,童年时候是有体验的,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我们这代新人都共同经受过。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教育改革的试验品,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改革开放的淘汰品。有个段子形容我们这一代人:长身体的时候,遇上了三年大饥荒;读书要上大学的时候,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要找工作的时候,赶上了上山下乡;要结婚生子的时候,开始实行晚婚晚育;从乡下回来,安排进了小厂小企业;刚过中年,就不得不失业下岗。这的确也是这一代人的真实写照。
一、
我叫李长勇,1949年出生,新中国的同龄人。我是六九年下放的知青,刚下乡时,弟弟才十岁,小妹妹也只有八岁。因父亲患矽肺病去世了,仅靠在矿里做小工的妈妈每月挣来的二十来元钱,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我下乡后,买油盐粮菜全靠自己挣钱来解决。那时,在农村一个强劳动力,一天的工资才九分钱,至于我这个半劳力就更低了。人,总得生存吧!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在山里生存,就只能打山的主意。
有一天晚上,社员上山偷砍树木,连夜扛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卖,我犹豫一阵之后,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我跟着一伙人摸黑去上山偷砍树木,谁知刚砍倒树木,准备扛走时,被巡逻的林场工人发现了。为了逃避被抓,我在仓惶之中跌进了一个土坑里,当场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苏醒过来发现右臂和右腿都受了伤,而且伤得很重。想喊,又怕招来林场的工人;想走,又疼痛难忍,更糟糕的是我迷失了方向。
绝望之中,我哭了。哭过之后,还是摸黑慢慢地爬出土坑,也不管后果如何,瞎乱地顺着山腰上的一条小道爬去。后来,我爬到一个岩洞,发现里面有人,便爬进去求救。
这家人共有祖孙四人,老公公见我伤重,听我讲明情况后,便同意留下我。然后,他用单方,找来草药为我治伤。
半月后,我伤愈拜谢了他们回到队上,恰好遇上只有一面之交的陈晓光,我便告诉了这次"落难"的经过,陈晓光听了大为感动。
第二天,他和女朋友春梅托人买了两斤糖来,要我同他们一道去找那个老公公。
当时,陈晓光是听我说:现在还有人住岩洞。又觉得这位老公公心地善良,应该好好感谢他,所以要我带他二人一起去看望老公公。
到了岩洞,陈晓光发现岩洞既矮又黑,洞内既无床又无什么家俱,而是谷草铺地作床、三块石头垒在洞口作灶煮吃的便是一个家。看见这祖孙四人衣服褛烂、简直不能遮羞,更为他们能救人而感动。又闻知这位老公公是烈属,儿子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牺牲了,每人每月只有三元的补贴。顿时,全身血液沸腾起来。
我和陈晓光、春梅告辞了老公公回来后。马上安排几个知青分别串连了二十多个当地的和外地的知青,各自准备三天的口粮,第三天在山下集合,准备搞一次"献光和热行动"。
第三天,我们二十多个知青由陈晓光指挥,当天就找了一块向阳坡地,平整出一块屋基来。晚上,又集体行动,上山砍了几十根树扛下山来。第二天,便分别做出椽子、桷子、房梁。与此同时,另一拨知青则挑土筑墙,三天就建成了一个有三间正房、一个偏屋的土墙房子。第四天,椽子上了、桷子也钉好了,却发现没有瓦。正当大家发愁时,一个社员说:“一个公社干部刚收到一汽车别人进贡的新瓦,可以去借啊!"当天晚上,我们便偷偷地把大队的手扶拖拉机开出来驶往那个公社干部家,先威胁要告发他受贿。然后,又劝他"行善"当一回雷锋,好说歹说,他最后同意送我们一万块瓦。于是,把那一万多块瓦由拖拉机跑了三趟拖回来,当晚就盖上了。第五天,便请那家烈属祖孙四人搬进了新居。
然后,陈晓光叫大家分别回去后不许声张,由他一人背着被子到县公安局自首投案,承担了一切责任。
由于这次违法行动帮的是烈属,又加上中央对知青陈晓光的来信作了批示:要对知青照顾、宽容,又因不少贫下中农知道这事后,纷纷联名向县革命委员会要求宽大陈晓光,最后县革委下令公安局无罪释放了陈晓光。
正是这段经历,我和陈晓光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而陈晓光因为这事,在全县知青中名声大震,成了知青们崇拜的偶像。
几年以后,也就是七二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趁着刚下了一场雨后的空闲,挑着一担刚分到手的谷子,沿着山间小路不顾路滑回家。
下过雨后的山间小路,很不好走,当我费力地爬上陡沟子,正想歇口气时,突然,看见前面有个人跌了一跤,并滚下了山下的河里。也许是那人被意外的一跤摔晕了或是他根本就不会游泳,只见他落进水后往上窜了窜,就叽哩咕噜地沉入了水底。
我看见那人沉入了水后,才回过神来,不顾一切地冲过去,一个鱼鹰入水跳进河里,几下冲刺游到那人沉水的地方。我迅速地换了口气,扎进河底,睁眼一看,见那人还在挣扎,潜到他背后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回身拖起浮上水面。当我把那人拖上岸,为他倒了水,又做了人工呼吸。见他有了呼吸后,我才发现自己挂着了河底的树桩、手臂上裂开了一条三寸多长的口子,血正不断地流了出来。
那人苏醒后,能说话了,我因伤口流血过多,加上伤口浸了水而痛得我说不出话。
我包扎好了伤口,谢绝了他要帮我挑谷子的要求,咬着牙把谷子挑回了家。
事后那人打听到我的姓名,马上在全公社乃至全区、全县进行宣传。于是,我这个舍己救人不留姓名的老知青被招了工。到地区学习半年后,七三年五月初被分配到我原来当知青的公社,当一名人保组(人民保卫组)的办事员,也就是现在的乡公安员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