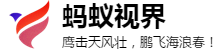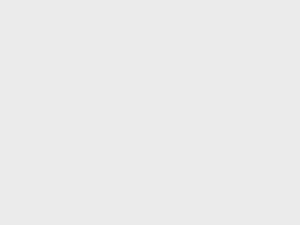- A+
清明如期而至。今天的清明节对于我们的意义无外乎三种:中老年人为亡者扫墓,重视者回老家祭祖扫墓;年轻人在清明节未列为法定假日时视若寻常,清明节成为法定假日后则把它作为可出行游玩的假日。
尽管不同年龄的人对清明节定义不同,但不可否认清明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它让那些掩藏在心底的对于死亡对于失去的恐惧和疼痛和伤感有一个合适的时机释放出来,它太轻易让人触景伤情,一点细雨,一条垂柳,一句诗,一首歌,一通电话,轻易的让人的笑脸变得僵硬伤感,轻易的让人流下眼泪。有些故事,只自己去思量的时候大约也只是感动伤心,若是讲给人听,便会在叙述中增添无数的悲苦而不自禁的流下泪水。
然若要让我回忆,我想的会是谁呢?我不愿意流泪,那便在记忆中寻找一些温暖的颜色吧。我八岁的时候爷爷去世,关于当时的记忆已经变得遥远而模糊了,冷风,飞雪,黑棺木,哭声,这几样构成了我对死亡有了最初的印象。年幼者有着岁月的恩赐,很快便可遗忘悲痛。然而,有些鲜艳活泼片段却永驻脑海,每每想起,便有股股暖意涌起。那个我已忘了是高大还是矮小的瘦瘦的老头,曾经充当我的“保姆”抱着我四处溜达,用身上仅有的两角钱给我买一包饼干。
曾在我摔得鼻青脸肿的时候亲自给我熬他的土方黑黑的熏人的膏药,不顾我的反对贴了上去,啊,效果杠杠的好-现在再也没有膏药了,只有老家那口黑黑的熬药的锅催我想起那时的情境;也曾在我闯祸“离家出走”的时候收留我。虽然我已忘了他的模样,连照片也觉得陌生,但我永远记得他。
春节,元宵,清明,中秋,以及每年的祭日,我陪着奶奶到家坟挨个的烧纸钱,这个是大太爷爷,旁边是二太爷爷,那个是太太爷爷,那片属于我家的坟地,陆陆续续增添了爷爷,三爷爷,大爷爷,还有爸爸。每一块坟我都去烧过纸钱,磕过头,放过“叫醒”的鞭炮。每一块坟我都去填过土,插过柳,然遗憾的是没有哪一个长出一棵树。不过乡野里从来都不缺野草。
春天有绿色的小草,夏天有黄色的蒲公英和紫色的紫花地丁,秋天有漫地的金黄的野菊花,我曾一个人在坟地的附近采摘野菊花---泡茶,做枕头,我一点也不害怕,至于冬天,也没有人会烧去枯萎的野草,在加上旁边树林飘来的落叶,一个个坟头被遮着护着,又有什么可担心的?
在这个本应念着“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诗的时候,我却想起了陆游的那句“死去元知万事空”,顿觉悲伤。死亡会带走很多,我们会忘记亡者的许许多多的事,但不可忘记铭记。唯有铭记方能证明先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