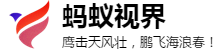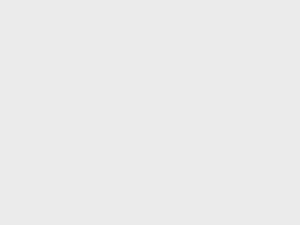- A+
石兰女同学,你好
北风吹,雪花飘,不知不觉,几十年的时光也便过去了。当年结联小学那群爱哭爱笑爱闹的小姑娘,现在都变成了爱唠叨,爱操心的老奶奶了。时光无情人有情,因为人是世界上的主宰。我真想找个机会,仔细看一看你,和你好好地聊一聊。
我想从你的脸上,看到我们小时候的影子,想从你的头发,你的眼睛,你的语言,甚至你的一举一动里,找到我们做孩子时的痕迹。我知道,我们已经老了,今非昔比了,但我仍然很执着,很坚持。我的印象中,你是不会老的,不管风吹浪打,你顶得住,一定是,依然旧模样。
我的父亲在结联学校当老师的时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那时候,我们都还小,好像也就是十岁样子,而且,我们两家人的经济条件,差极了。我们全家住在学校狭窄的木板房里,你家,则住在离学校约一里地的下结联村。可贫穷的日子并没有让我们贫感情,我们两个一起读书,一起上课,一起做作业,一起睁着眼听大人讲故事,形影相随,就像亲姐妹一样。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时候的我,已经担负起家里的很多家务。我得去上山砍柴,早上得早起,给家里打扫卫生,我得做饭,我得洗碗,得洗衣服,还有,我得给我的那个残疾人弟弟阿三,擦屁股,端饭,端水。
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就在父亲紧凑的催促声中,匆匆忙忙起床。我必须尽快梳好我的头发,尽快洗脸,尽快作好所有的准备工作。然后,我就去做那些繁琐的家务事。年年如此,天天一样,早上那段时间,我很忙,也很辛苦,但我总是忘不了偷偷地朝着学校外面望一望。外面有什么好望的呢?穷乡僻壤的,除了鸡叫就是狗叫,就是那些歪歪斜斜穿着衣服的大姑娘,小媳妇去河边洗菜,那有什么好望的。我是在望你,望你在那个时间来学校上课了没有。
你总是像瑞士手表那样,很准时地出现在小路上。那时候的你,穿着一件麻黑色的家机布衣服,背着一个蓝色的自己缝制的书包,你的头发梳得很整齐,一根辫子吊在后颈跟上,像是黑色的仙果。你的眼睛像葡萄一样,很明亮。我喜欢看你在小路上徐徐走路的样子。寂寞的小路,枯燥的小路,因为有了你的缓缓前行,竟热闹起来。金色的太阳出来了,鸟儿在歌唱,就连路边的那些野花,小草,在山风的吹动下,也点头哈腰的,像是在欢迎你。凉爽的清晨,你是那条路的路神,路仙,小精灵。那条路,因为有了你,风光无限。爸爸总是在责怪我,爸爸说:“张文利,你又在东张西望的,看什么去了?”我总是头也不回地说:“爸爸,你莫打岔,快要到上课时间了,我在看我的好朋友石兰女呢!”
你总是不忘记从家里带一些吃的来给我吃。什么包谷粑呀,什么板栗呀,什么柚子呀,还有红薯什么的,对了,记得有一次,你还给我带来了黄灿灿的,过年才有的“黄雀肉”。我们在一起吃东西,一起面对面地坐着说话,有时候还一起唱着刚学来的歌曲。班上的那个男同学石文照,讨厌极了,他总是欺负我,扯我的书包,拿我的作业本,还做鬼脸来气我。我惹不起他,但是你每次都站出来保护我,看你的那个气势,谁要是欺负了我,你就会和谁拼命的。夯子照村的杨老师说:“怪了,张文利的作业和石兰女的作业,怎么会一模一样,要么就同时对,要么就同时错,怪了。”我说:“杨老师,那有什么怪的,这叫‘姊妹篇’,姐姐妹妹有特殊感应”。我妈也说:“这两个孩子,一天到夜就那么无忧无虑地玩啊玩的,玩得个昏天黑地,你看看,天是她们的,地是她们的,这样子,全世界都是她们的了,菩萨说,这是前世的缘分。”
我那时,常常看着你发呆。我想呀,我一定要和你做一个好伙伴。是的,一定要做一个好伙伴。我们一起读小学,一起上中学,然后一起读大学,再然后,我们一起入团入党,一起参加工作。还有,等将来呀,我还要在你家的旁边,修一间小小的房子,木板房,到了晚上,我们就坐在家门前一起数星星,看月亮。那才叫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呢!
但命运总是这么的在我们之间作怪,上了中学,老天爷便把我们分开了。你去了吉首二中继续学习,而我,听从了命运的安排,为了养家糊口,去了医院上班。
没有你在身边的生活是寂寞的,乏味的,但这是命,不习惯也得习惯。可我总是忘不了你,常常想和你手牵着手,像两只蝴蝶一样,一起飞呀!跑呀!笑呀!有了这些幸福美好的记忆,我觉得我的人生充实,快乐,美满……
我真想,有那么一次机会,我们能够像美国佬那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叫你姐姐,叫你妹妹,叫你老同学,我还想紧紧地握着你的手,永远永远不松开。真的,我好想好想,好想好想。
兰女姐姐,兰女妹妹,老同学,生活有时候免不了出现一点点阴差阳错,免不了有一点小插曲,一点小误会。我记得有一回,我到人家屋里做客,喝多了酒,稀里糊涂地回到了家,迷迷糊糊地倒在床上。外面,好像有人在敲门,隐隐约约,听声音又好像是你。不过,那该死的酒精已经把我的脑血管膨胀得天旋地转了,我不能站起来看看是谁,也不能问一问是哪个,就算问了,也分不清楚是谁……我像一头被屠夫杀死了的猪,一头四百斤的大猪,睡在床上,不能动弹了。
世界上最重的担子,不是千斤重担,而是心尖上有着内疚。世界上最不想说而又最想说的话,不是钱有多少,而是对不起。这件事让我时刻耿耿于怀,无地自容,我真后悔,千怠慢万怠慢,我也不该怠慢你呀。
我去了建筑工地,看到岩匠师傅在用钢钎撬石头,我想呀,这钢钎要是能帮着我,把那天的失误撬回来就好了。可岩匠师傅告诉我说不可能。我也抬头问了星星,问了月亮,我说:“星星啊!月亮啊!你们给我说句话呀,哪怕半句也行啊!我以后再也不敢喝酒了,吉首人讲:千丑万丑,女人喝酒,我以后真的不喝了。”但星星,月亮都不讲话,它们好像不愿意理我。我还去了庙里,烧了香,拜了菩萨,可菩萨说:“缘分缘分,又要有缘又要有分,这人世间的事情,前因后果的,还是顺其自然的好”。我说:“菩萨啊!我是处处小心翼翼啊!平日里,萍水相逢的人,我都把人家当朋友,何况我生生死死的好姐妹?”
这件事在我的心里变成一块病,一块心病,病得我抬不起头来。同时,它又是一个疙瘩,一个死疙瘩,缠得我喘不过气来。它像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重重地压在我的头上,我真想找个机会,把这石头卸下来,甩得远远的,甩到太平洋,印度洋去……
好姐姐,好妹妹,你能够原谅我吗?你能够原谅我的那次错误吗?那次,是我不对,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柏林墙被推倒了,东德西德合二为一,朝鲜半岛也实现了南北对话,祖国的宝岛台湾,也将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和平统一。我们那点事,鸡毛蒜皮,算不了什么,说白了,也就屁大点事,有什么了不得的……
我含着眼泪,把我的事情掏心掏肺地,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昌满同学。我说:“昌满同学,这是一种烦恼,搞不好,我会永远为这件事痛苦的”。昌满同学说:“没关系的,张文利同学,希腊有个哲学家叫季诺,当有人问他什么是朋友时,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朋友,就是另外一个自己’,石兰女同学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同学,她人品好,口碑好,人格魅力也很好,你放心,你们的同学情,姐妹情,打断骨头连着筋,不会因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受影响,你们的友谊应该是毫发无损,稳如泰山。”
真的好感谢昌满同学,他的三言两语就让我茅塞顿开,我高兴极了,这叫拨开乌云见青天。于是,走出大门,对着大街高喊:“石兰女,我的好姐妹,我张文利想念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