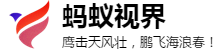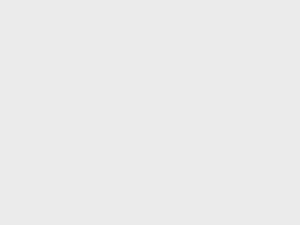- A+
一九七三年夏,母亲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船队,带着我们兄弟两人迁居黄陵镇。沌口船队在那块土地上创建了织带厂和电子管厂,一大批年轻的船民成了工人。
黄陵比沌口规模要大,也是东荆河旁的镇子,人口多,有一条较长的老街,地面铺着青条石,是镇里的主要人行道。街边立着各个时代的建筑,大量的青砖黑瓦房诉说老镇的悠远岁月,还有较纯粹的木头民居和一些新式的红砖瓦屋。一条紧邻老街的碎石路,是手扶拖拉机和汽车的通道,路旁一块伸进水塘的荒地上建筑两排红砖瓦平房,那是船民的新家。老街另一边的一个小巷直通船队的工厂。两厂相邻,电子管厂出品的东西,只是在一节白陶瓷管外螺旋般环绕一根细细的金属丝,两端系在铜片上,表面烧上绿色的瓷釉覆盖,这不是好玩的东西。织带厂内,电机带着一人高的机器摆动,两头尖尖的梭子在一排细棉线中飞快的来回穿过,机器的撞击声冲击耳膜,空中的飞絮混杂灰尘。母亲进厂成了纺织女工,打扮俨然像一个护士,白口罩、白工作服、白帽,秀丽的长辫剪成了齐耳短发。
那一年,我们这些船民的子弟开始游荡在黄陵的大街小巷,一块陌生的土地渐渐变得熟悉。大概船民是穷走江湖的行者,又占了黄陵的地盘,便遭了人家的白眼,大人的情绪感染了他们的孩子,青砖黑瓦的老房子的大门口,几岁的小孩子盯着我们这群从船上来的顽童,用稚嫩的童声从牙缝里蹦出四个字:“云梦赖赖!”
船民们彻底地赖在黄陵不走了,要在这扎根。老街的一头是一所小学。八月,姑送来了亲手缝制的灰布书包。九月,我们兄弟俩坐进了学堂,我一班,他三班。从此,我和四十几个同龄的孩子整齐地坐在一间大房子里,见了很多陌生的老师,读了很多称为课本的书。我的第一任班主任姓罗,是一名年轻而亲切的女数学老师。那时我们学计算、拼音、认字,学期末评为三好学生,班主任奖励一根铅笔和一个写字本,还有一张写有名字的奖状。班主任常换,后来换了一名年轻的姓雷的男老师,因为他布置的作业最难完成,同学们背地叫他雷达。
文革期间的学校学习远远不是现在的模样,小学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下午老师带着孩子们扛着小锄头小铁锹到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挖黄土坡,把荒草地整理成良田,种植芝麻,水稻。黄陵的土壤色黄,肥力贫瘠不济,老师给学生布置的作业不是写字而是拾肥,每人都要上交规定数量的牛粪猪粪,这是最痛苦的差事。休息日我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竹筐走遍黄陵的荒郊野地河坝田埂。几百学生拾肥,哪有那么多牛粪猪粪啊,见了一点干瘪粪肥如获至宝,一边用铁锹小心翼翼铲进竹筐,一边念叨“积少成多”;见了耕田的黑牛,便提着筐跟在牛屁股后面走,望眼欲穿。筐里积满了收获,便兴匆匆送往学校,雷达推窗瞟一眼,估量一下重量,嘴一瘪:“二十斤”,从来不多说一点,全然不体恤压歪的稚嫩肩膀。我估计那段日子,黄陵镇环境最干净。
到芝麻地抓青虫是一件有趣的事。土岗上的几亩芝麻地不知从哪跑来了那么多肉坨坨的虫子,把翠绿的芝麻叶咬得千疮百孔。我们每人折叠一个纸盒,把一个个青虫装进去,老师要清点每个人抓虫的数量看是否完成任务。
听说蜈蚣是一味中药材。汉阳三中后面的高山叫朱山,对着学校的一面山坡平缓,翻开一块块石头,不难见到肥硕多脚的蜈蚣,我们学着老师的样子用铁镊子夹着头毫不畏惧抓住它,拔掉它的毒牙。失去武器的蜈蚣老老实实在手中爬行,成了玩物。长长的蜈蚣用竹签绷直晒干,制成药材。
种稻的水田是一个大工程,黄土坡挖了几年才种下青苗。去田里拔草和稗子是一项重要作业,但我始终怕水里的长蛇和蚂蟥。
忆苦思甜是那时常见的政治课。有时不知从哪请来了一位大爷,白发苍苍地坐在会议大厅的讲堂上,给全校的师生讲旧社会所过的苦日子。我们在《白毛女》和《半夜鸡叫》里领教了地主的可恶,但要我们从眼缝里挤出几滴眼泪来不太容易,而吃糠咽菜吃窝窝头确实是我们的向往,那也许是美味的食品。
忽然学校不知从哪砍来许多鲜嫩的松针,在教室外的空地用红砖支起几口大铁锅熬汤给全体学生喝,老师说喝了可以防治传染病,那恶心的药汤不知喝了几碗。那时人们没有免疫针可打,也许当时正流行什么瘟疫。
养蚕是课后的爱好。回家的路边有一株粗矮的桑树,爬上树枝摘一书包鲜嫩的桑叶,是每天必做的事。芝麻粒一般的籽里钻出来的小黑虫只吃桑叶,不碰蓖麻叶莴苣叶。小虫一直不停啃食叶子食量极大,每天带回的桑叶吃得仅剩下乱七八糟的粗叶脉。小虫有一个蜕皮的过程,开始昂着头僵硬不动,蜕了一层皮后似乎摆脱了束缚长大了一点,如此三番丑陋的小虫变成白玉一般的蚕宝宝,肥嘟嘟煞是可爱。更奇怪的是有一天玉蚕不肯进食,身体变得有些发亮,皮肤起皱,开始吐出细丝把自己包裹起来,细丝形成一颗椭圆形的白茧。茧的用途很大,可以抽丝做成华丽的衣裳。茧一般色白,我的金脚蚕能吐出黄色的茧,粉色的茧极少碰到。一段时间后蚕蛹破茧而出,羽化成蝶,实现生命的一跃。
黄陵有织麻的传统,那时常见当地不少人家纺麻。去同学家学纺麻是一件辛苦活,木制纺机摆在屋外,我拉着长长的麻线绕着给机器送线,小手的关节被麻线勒出血印。养小鸡也麻烦,毛茸茸的鸡雏围着腿脚转,一不小心踩成跛脚,最后甩给母亲伺养。坚持得比较长久的是玩水。游泳是船民的基本功,有些彪悍船民的水下功夫虽没有浪里白条的本领,但风里来雨里去练就的生存能力不容小觑,一个猛子扎过河显得平常,直直地平躺在水面不沉让人惊叹。耳濡目染,船民的后代似乎见了水就亲切,下了水就得心应手。下午放学早,几个伙伴相约去河里游泳。老街连着东荆河,那时黄陵没有桥,一艘铁驳渡船把汽车行人送往彼岸。我们一会儿在岸边戏水,一会儿坐着渡船行至河中央,再游往岸边码头。母亲严厉禁止,我便每次玩水后晒干了衣服回家,但背上的泥巴暴露了行踪,仍然挨了不少板子。
大人们的游戏更有气势。公路上常常有游行的队伍走过,有时见纺织女工停下手中的工作走在游行队伍里,队伍的前面举着红旗,人们喊着“批林批孔”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我们这些小伙伴跟着队伍跑,跑得一身臭汉就去水里洗。偶尔也见几辆大卡车驶过,车上前排几个人双手反绑,头顶插着木头标,上面写着什么流氓罪或者反革命罪,身后站着几个持有长枪的穿绿军装的民兵,车顶架着一挺机枪,黄橙橙的子弹排从枪身落到车顶上。据说游完行以后拉去枪毙,道路两侧围观的人们不敢大声讲话。有时,也见两个民兵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走过,那人胸前挂一个红薯或者一瓶白酒,身后必定跟着一帮嘻嘻哈哈的小孩。
最威风的要数在校门口站岗。毛主席逝世,学校开追悼会,场面肃穆,几个红小兵身穿白衬衣手持木制长枪在校门口站岗,检查进出的学生衣领衣袖是否整齐。这是一段得意的日子,每个进校的学生流露出羡慕或者害怕的眼光。
一天,班里的数学老师调走了。校长的千金刚中学毕业,来一班临时代课。千金讲完例行的课,接着就讲知识拓展。
“负数!”
千金得意地在黑板上写下“1”,前面加了一个减号,唬得我们一脸无知,我怀疑那是极深的学问。
学校不过如此,街上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去处,只有一家小小的书店尚值得一逛。书店内玻璃柜里摆放着几本册子,和一些白底红字的《毛泽东选集》、《论持久战》,还有几本小儿书。几分钱一本的图书有图有文字,成了我的最爱。我成了书店的常客,几年间用极其有限的硬币积攒了几十本连环画。读它也学着画它,连环画成了我了解世界的窗口,我读书的习惯大概是从读小人书开始养成的。当书店的玻璃柜里出现《连心锁》、《红旗飘飘》等大部头的故事书时,自然我成了它们的小读者,它们的内容更丰富,故事更曲折。我的目光开始探视抗日前线和抗美援朝的战场,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我的阅读一发不可收拾,就像徜徉在春天花海的一只蜜蜂,吸取每一朵飞过的花儿的甜甜蜜水,《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进入我的视线。
有一年暑假快结束,我从沌口坐机动船回黄陵上学。船分两层,因为一个亲戚是船上的水手,他安排我进顶层的船舱休息。船行驶在东荆河,我无聊地躺在床上,见枕头边用布很随意地包裹着几本厚书,书的头尾露在外面,纸质稍微发黄。我好奇打开布包,只见深红色的书面赫然印着三个黑色魏碑体的大字:红楼梦,书一共四册。这是我第一次遇见《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的介绍文章里提到这部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大名鼎鼎的长篇小说。我捧起书来读了几页不知道什么意思,对它的接受度远远低于其他故事书,不能一下子抓住我的心。十年以后我再捧起《红楼梦》的时候,被它优美而哀伤的文字吸引,一遍又一遍读它,它的神韵深入骨髓,我就像一个婴儿一边看着母亲的脸庞一边饱饱地吸取乳汁。直到今天,《红楼梦》是我读过次数最多的书之一,它在我的枕边榻上,中国最优秀的文化一直滋养着我。
2017年3月11日,孝感